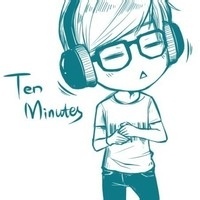四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虚掷
四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虚掷
这个早晨很早就醒来了——八点钟,相比以往八点半才起床的日子,因为要去医院看病。我从窗户向外面看了看,夜色还如此深沉,丝毫没有半点天亮的迹象,世界仿佛在这沉沉的黑夜中永远睡去了。即使已经有很多楼房的灯亮着了,也丝毫没有冲淡黑夜的力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看见这样近乎夜色深沉的世界,心里难免对生活对人生感到一丝疲倦。这是我不喜欢冬天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它的寒冷,就是这早起所要面对的夜色。洗漱之后穿好衣服,我出门了。街上一片安静,没有出租车,也没有行人,我只好自己步伐朝医院走去。不过五百米的距离,一个人独自面对这黑黢黢的世界,心里总会生出一些失落,好像我被世界真正抛弃了,似乎我离开了人类的文明,向着无穷无尽的永夜走去。路灯昏黄的灯光模糊的照着雪地,雪,也在沉睡中。只有路边的树木陪伴着我,它们光秃的树干和枝条也被黑夜吞噬的很多。我是向着西面走去,借着黑夜,我看见了东方穿破黑夜悄然升起的黎明。

夜,如此漆黑,那暗红色的黎明越发梦幻。一颗明亮的星从东方升了起来,刚才我透过树林向这颗星看去,以为月亮还未落去呢。这明亮的星,闪耀着异常夺目的光。偶尔有两三个早起走在上学路上的学生。这就是大地的全部,此刻,我并不是它的居民,只是它匆匆而过的游人。我把自己的目光努力的扫向远方,我是企图寻找夜色中的群山,那群山有时候于我也有一种指明灯的作用,给我指引着方向。夜色如此深沉,即使黎明女神已经把这黑色的幕布撕开一个缺口,也不足以驱散黑暗。这样的路程,多少会让我记起往昔的冬夜。我想了今年夏天去逝的表哥,想起二十六年前,少年的我和父亲一块乘车去石河子团场参加表哥的婚礼,我们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日子,那时交通不便,车辆非常稀少。我和父亲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赶到团场的车站,坐上回去的车辆。姑姑和表哥把我们送到车站。夜也是如此漆黑,团场仅有的一盏广场灯,发出惨白的光,照在的雪地如此苍白。从那之后,对于寒冷对于冬夜,深深的刻画在我的记忆深处。这如此许多年过去了,不知为什么,当我独自一人走在这样寒冷的路上时,就忆起了这些并不精彩却很耐人回味的片断。我很清楚,生命终将流逝,现在父亲越发苍老了,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日子可以守望,守望那些纯真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群山慢慢地从黑暗中显出一丝深蓝色的轮廓,我的生命也并非能永远与它厮守。这样想着,心间涌起一丝宁静的幸福,做一个大地坚实的守望者,跟随着大自然的轮回看见世间的沧桑,我也该明白,什么才是生命应该执着追求的,也总该通过另一种方式让自己的生命在大自然的永恒中留下一丝印迹。黎明,继续把自己的曙光向天空扩大。我走了一段夜路到了医院。

窗外,阳光朗朗的照着,别珍套山就在我眼前高耸着,满山的积雪,不知是为谁愁白了头。我站在窗边,仔细向它望着。我用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着它的每一座山坡和每一个山峰。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除了阳光照着雪地反射出的光芒,便只剩下令人窒息的寂静了。连在山间停留较久的牧人也已经把它遗忘了,连着山脚下的荒野,它们仿佛遗弃在世界遥远的角落,从此以后,不再有人记得这里。那些生活在山间的野兽,不知隐藏在何处。不知谁家的狗,迅速的奔跑着穿过雪地,它狂吠着,跑向南面。另有几只狗,听到这吠叫声,仿佛接到了不可违抗的命令,也如此这般的向着南面跑去。它们的吠叫声,打破寂静,带来生命的回响。太阳已经升到正南面,狗的吠叫声渐渐地消失在荒野。